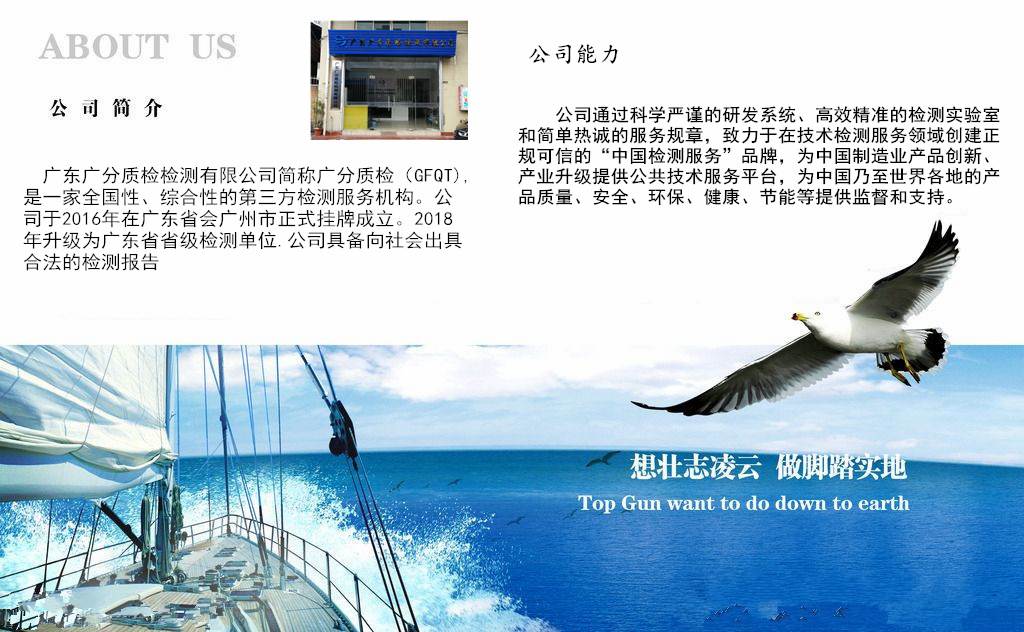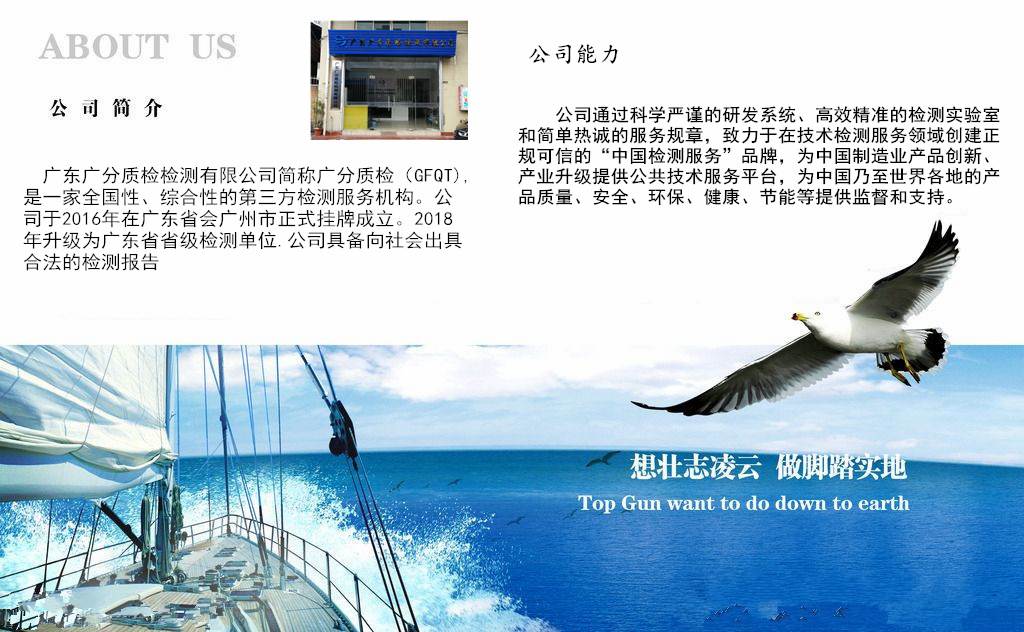
池塘底泥淤泥限量有害物质分析中心:
针对雷竹林有机氯农药六六六(HCH)残留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开展了雷竹林土壤HCH 原位生物修复及修复菌剂(BHC-A)对雷竹新陈代谢及生理活性、竹林土壤养分活化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BHC-A 原位降解HCH 效果显著,降解率高达85.25%;BHC-A 使用后,处理A、B 较对照雷竹叶片叶绿素SPAD 值分别提高12.82、11.36,根系活力分别提高了37.77%、24.25%,处理间差异显著,说明BHC-A 可以提高雷竹新陈代谢及生理活性;BHC-A 生物修复过程中,与对照相比,处理A、B 土壤pH 值分别下降了0.40、0.14 个单位,土壤水解氮分别提高了80.33、62.67 mg·kg-1,差异达显著水平;处理A 土壤有效磷、速效钾较处理B 和对照分别提高了33.02、36.98 mg·kg-1 和27.91、29.33 mg·kg-1,差异达显著水平;不同处理间土壤有机质及全效养分变化不明显,即BHC-A 可以促进土壤养分释放,提高养分生物有效性。
有机氯农药主要是指六六六(HCH) 和滴滴涕(DDT),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因其具有毒性强、化学性质稳定、降解难等特点[1],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2-3],特别是土壤污染[4-5],仅我国被污染的土壤面积就已超过了1 400 万hm2[6]。因此,采用适当的方法去除残留于土壤生态系统中的有机氯农药,对于农产品和环境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雷竹(Phyllostachys praecox C.D.Chu etC.S.Chao)隶属禾本科竹亚科刚竹属,具有出笋早、笋味鲜美、产量高、效益好等特点[7-8],是我国重要的笋用竹种。在我国雷竹主产区,雷竹林多是由原来的农业耕作地,特别是水稻田发展起来的[9],因其农药使用历史长、剂量大,致使目前的雷竹林土壤有机农药残留普遍,HCH检出率达100%[10],含量最高可达31.8 μg·kg-1,虽未超过国家标准,但其生物活性和移动性较高,致使部分竹笋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50 μg·kg-1)[11]。而近年来,雷竹林经营强度的增大及大量化学品的使用,致使HCH 生物活性和移动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导致了雷竹生长活性的降低和竹林土壤环境改变,乃至劣变退化。目前有关雷竹林农药污染土壤生物修复研究尚属空白。本研究针对雷竹林生态系统有机氯农药污染的现实问题,着重开展有机氯农药原位生物修复及修复菌剂对雷竹生理活性、土壤养分活化影响的研究,旨在为竹林可持续经营与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模拟土壤气相抽提技术(Soil Vapor Extrb, SVE)通风处理甲苯、乙苯、正丙苯混合污染的黄棕壤,研究了不同通风流量、不同土壤含水率、间歇通风等因素对目标污染物去除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通风流量和含水率是影响去除率的重要因素。当柱径14 cm、土壤粒径为10 目连续通风时,最佳通风流量为0.15 L·min-1,最佳含水率约17.98%条件下,甲苯、乙苯、正丙苯的去除率分别为99.84%、99.45%、98.25%,总挥发性有机物(Total VOCs,TVOCs)去除率达到了99.30%,且优于间歇通风;含水率为6.01%、24.73%时,TVOCs 的去除率仅为63.03%、89.03%,表明含水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VOCs 的去除;苯环上支链越长,分子量越大,沸点越高,越难以被脱附去除,反之亦然,表明有机物的分子结构和大小也是影响通风效果的重要因素。
我国场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区内将置换出大量工业污染场地,这些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占有较大的比重,如不加治理或修复而直接使用将存在很大的环境隐患和人体健康风险[1]。
土壤中VOCs(如苯系物难于生物降解,不累积于食物链,但对土壤与生物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直接导致白血病的发生)[2]作为一类特殊的污染物,因具有隐蔽性、挥发性、毒害性、累积性和多样性等污染特性[3],被列为环境中潜在危险性大、应优先控制的毒害性污染物[4]。许多发达国家已明文规定,对受VOCs 污染的土壤必须进行妥善处置,以保证生物和环境的安全[3]。
土壤气相抽提法(Soil Vapor Extrb,SVE)是一种向污染区域通入新鲜空气,将VOCs 从土壤中解吸至空气流并引至地面上处理的原位技术[5]。因其高效性[6]而广泛应用于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场地的修复。本文以VOCs 中危害性较大的甲苯、乙苯、正丙苯为目标污染物,研究了通风流量、含水率、间歇通风等参数及目标污染物性质对其去除率的影响,分析了通风前后黄棕壤中甲苯、乙苯、正丙苯的衰减规律。